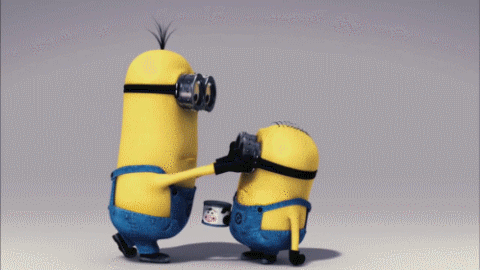[分享]西安,西安,可否长安?
作者: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
![]()
封城下的西安街道
岁末年初,又一波疫情袭来,这一次罹祸的是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镐京,是包括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在内的十三朝古都;堪称中国四大古都之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1981年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也是美媒评选出的世界十大古都之一。如今这个地处中土的文明发祥地以令人难以形容的姿态进入抑或尚未充分进入公众视野。
(一)
12月23日西安封城。目前疫病确诊人数已近2000例。主媒、公媒、自媒传出的消息以各种方式让人唏嘘、让人感叹、让人揪心,让人无以言表。人们对西安人的关切和对疫情管控的评论文章已经不少,概括起来大致有几个方面:
一是救治防控不利。
患者孙辉在12月21日出现“发热、头痛、眼痛、咽痛、腹泻”等症状,一连五天呼救,要求隔离住院治疗,打遍了110、120、12345、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街道办、社区电话,结果却是各种推诿、耽搁、失联、踢球,“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直到一家六口全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不该隔离的强制隔离,已经发病的不予隔离;相比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此可谓“真真错杀一千,偏偏不管一个”。类似的案例还有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检测、隔离、送医等环节的低效低能却是有目共睹。以至于有网友发文指出:“在这持续两年的抗疫生活中,我们整个国家抗疫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多地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累积了诸多的应急预案,面对疫情,多数省份都能从容应对。……而西安,却似一个从不知疫情为何物的城市,疫情到来的时候,给外界的印象是,面对疫情的来袭,所有人惊慌失措,所有部门束手无策,甚至搞出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与两年前疫情突发之时,抗疫经验匮乏,时间急迫相比,西安有些人,简直就是渎职,……这是对疫情的严重失察”。
二是强制管控失当。
疫情防控中过多强制性、甚至使用暴力的情形已是屡见不鲜。居住在城中村的“西漂”小伙,因数日缺少食物饥饿难耐“违规”外出买了一袋馒头回来,在防控点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被数人围殴。馒头散落一地,人们的心也碎了一地。
另一位年青人因为下楼买吃的,被防控人员强迫视频认罪,但不知这些声色俱厉的防控人员的权力是哪来的:莲湖区在周日晚有一名青年因为家人多日来吃不饱,偷偷逃走出来帮家人买食物,被监控人员当场抓住了,之后被逼在镜头面前认罪,公诸于世。监控人员还不断训斥他。
一些地方,一例感染,全员拉走,送到郊外隔离。且不说隔离场所基本生活条件无法保证(饮食、保暖等),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扎堆检测、集中运送、集中居住就会大大增加交互感染的机率。这种做法置民众生存和健康于何地?
封城十天之后,西安宣布要在一月四号达到社会化清零,“这里所说的清零,就是除管控区和隔离区以外,再无新增病例”。不知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做出的定时定点清零策略所依何据?又如何实施?这里有一个问题:病毒听谁的指挥?
紧接着,1月5日西安发出通报:西安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病毒还真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
西安孕妇流产事件(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三是人民生命损失、生计困难
由于疫情防控中权力的强制性缺少限制、行使过当,造成本不该发生的悲剧,这是最令人痛心的。
从12月26日傍晚开始,西安市政府下令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全面消毒作业,派出大批人员和消毒车到处喷洒消毒水,而当天气温低至零下5-6度,导致路面喷洒的消毒水迅速结冰,结果引发了车祸,造成车毁人亡。
名为“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父亲心脏病发作,多方呼救求助,虽然费尽周折送进医院,最终还是因“耽误太久,抢救失败”。她泣告大家:“我没有爸爸了”(年仅61岁的爸爸)。
一位怀孕八个月的孕妇就在医院门口苦等二小时后流产,亲人痛彻心扉,网络几近沸腾。
病患、老人、孕妇因防控得不到救治,同样是人命关天。这样的案例并非绝无仅有,姥姥、爷爷、外公、怀孕九个月的临产孕妇都在其列:
隔离防控要保证基本的物资供应,否则会造成不亚于病毒带来的对生命健康的危害。而一声令下的封城封区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安排和保障。因食物匮乏求救求援的帖子非常多,每一个帖子中提到的情况都令人心酸:
今天(3日)网友发给我一段视频,视频中显示一名男子躺在居民住户门前,旁边有身穿工作服装的人在问话。因为说的是方言,听不太清楚说的是什么。网友在文字中表示,这名男子住在东韦村子。因为一天就吃一顿方便面,低血糖晕倒了。
一位网友在微信群里表示,做核酸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单元24楼的一位老爷爷,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
一位身居未央区凤城四路的网友昨天(2日)“紧急求助”,家里两个多月的婴儿,太太没有母乳,但是奶粉已经断了5天了。快递都被卡了,110让他找防疫办,防疫办让他找街道办,街道办让他找12345市长热线。12345做了等级,但是中间等了4天,打了无数电话,最终还是告诉“等待”。这位网友表示“求志愿者也不行,不让出小区”。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网上根本抢不到东西,目前孩子在“喝米汤”。
还有那些非西安居民的打工者,城市中无住处,有家却不能回,天寒地冻,食宿无着,在街边徘徊。
防控本是抵抗病毒、保护生命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力运作方式却导致生命健康的损毁,实在是本末倒置。
四是信息不畅,不可批评
我想这方面网友们有目睹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仅此一贴可见一斑:
仅一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即可了然。
(二)
说到防疫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人们除了关注现象当然也要加以分析评论。与以往遭遇重大事件或灾难时通常的归因相近,大体不外乎如下几类:
一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防疫过程中出现的强制甚至伤害被管控者的事屡见不鲜,通常被视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语言不当等;即使事后向受害者道歉也多是从作风粗暴上检讨。但认真想一想,为什么本身并非强者却不同情而是欺负更弱者?为什么有一丁点权力就会滥用?这难道只是“用力过猛”的问题吗?
二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只重形式、数量不管质量、效果的统一运作、统一动作,不顾一地一事特殊情境的一刀切,都被归结为官僚主义作祟,导致整个机制运转不灵,顾此失彼,进退失据。如此,无法得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哪个层级、哪个领导应该担责,似乎都在恪尽职守、全面准确地执行上级规定,出了问题却谁也不负责,一股脑推给谁也不认识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完事。但细想一下,每一级管理者都仰面向上,唯上是从,把手段和形式当成目的,谁会为百姓的生命健康担当责任呢?
三是领导无能、水平太差。
有批评者指出:基层工作人员付出最大,最冷,最累,风险最高,还要直接面对群众。但是决策不佳,代价极大,属于顶层的锅。实可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话虽有理,但难道是所有的领导水平、能力都差吗?若如此,他们当初是怎么登上岗位的?遇到危机时谁能做主?谁来负责?
四是“系统性溃败”。
这可能是最深入的、结构性的概括。系统性溃败主要表现为“此次失控,不是一区一点的失败,而是整个系统设计,方案预案,上下执行串联,指挥调度,全盘的失败”。是“疫情以来,全国核心城市最大最愚蠢和最让人失望的抄作业不及格案例”。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如果是“系统性溃败”,意味着之前存在未发生溃败的系统、即可以正常运转的系统,只是在疫情突然来袭时发生溃败。但事实上之前就真的有运行良好的系统吗?
综上种种,说得都很有道理,但似乎都还在现象层面,尚未说透。这里我们需要社会学所强调的社会结构的视角,即从权力的结构、权力的本质、能力和绩效等角度进行分析。
(三)
我们先从几位“牛人”的案例来提出问题,这就是疫情导致封城时发生在西安的被称为“铁人三项”的令人心酸的故事。
一 是铁人越野
说的是步行哥,当他12月16日听说要封城,考虑到自己在西安无房无钱,而据说隔离费需要5000元,感觉还是回老家隔离好一点。于是从西安咸阳机场徒步开始进入秦岭山区,多次躲避沿途镇、村疫情监测卡点。直到在12月24日进入宁陕县被发现。步行哥在环境恶劣的秦岭山区足足行走了八天八夜,走的羊肠小道,没有后勤补给,没有地图导航,翻过茫茫大山,趟过冰冷河水,翻越了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目前这位步行哥已经通过视频公开认错,并把逃出时穿的鞋子和携带的箱子称为“作案工具”)
二 是铁人自行车
说的是骑行哥,他在12月22日下午得知西安即将封控的消息后,当晚直接骑了一辆共享单车,从西安莲湖区出发夜行10个小时,在零下十余度的气温下,顶风上坡连续骑了一百多公里,沿途还要躲避疫情防控检查。次日6时许,行至某疫情防控点附近,为逃避疫情检查,将自行车丢弃在路边,绕道进入咸阳市淳化县境内。
三是铁人游泳
这位游泳哥在12月27日从兰州坐高铁到达杨凌并住宿。因疫情管控杨凌通往周至的渭河大桥交通管制。28日游泳哥为了回周至老家,毅然在严冬之际,冒着冰寒淌水过渭河,结果陷在河道滩地淤泥之中6个小时,后被周至村民和工作人员施救,做完核酸检测后被送回家居家隔离。
这几位并非铁人、超人的普通人为什么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逃离疫区?他们在逃离什么?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风险是病毒还是其它?
对于逃避管控(并失败)的问题,人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在强大和有效之间划上等号,对于无所不为和无所不能之间的距离不能理解。
这里我们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就治理权力的不同面向加以探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把权力区别为强大有力和弱小无能的类型,这就容易形成一个误区:规模越大力量越强的越有治理能力和绩效,反之则越缺少能力和绩效。这个误解是怎么形成的?主要是没有区分专制权力与基础权力。
颇具影响力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长期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权力的本质,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概念:基础权力是指国家渗透于市民社会,并在社会中实施自己的合法的政治决策的能力。它一般是通过科层组织系统、以常规化的方式运作的。而专制权力则是指用一种非常规的专断方式所使用的权力,主要是应用于镇压和社会动员方面。(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1984)
有了这样一对概念,我们就可以了解权力的结构、特性及其间的张力。身大力魁并不意味着就有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个小文弱也不一定治理能力就差。起决定作用的恐怕不在大小而在性质。举例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帝国(王朝)体制的典型特征就是“专制权力”很强,而“基础权力”很弱。
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但就专制权力与基础权力的关系而言,新的政治体制仍继承了帝国体制的某些特征。在这种体制中,专制权力很强,但进行常规化运作的基础权力却相当弱。二者之间依然极不平衡。
政治学家邹谠指出: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总体性危机”,即政治体制解体与社会解组相伴随的全面危机。历经沧桑而建立的新政权,是解决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这也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或许可将这种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模式称为“总体性社会”。(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性社会中的政府并不是一种消极政府,而是一种超出常规意义的积极政府,而且当然是超强大的政府。如此,在专制权力与基础权力之间、在要管的事情异乎寻常地多和管理能力相对地弱之间、在权界与权责之间、在表现与实效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决定了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特征。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跑题千里了,而且太过学术。其实以切身感受稍微思忖一番便不难理解。(我也只能这样了,您懂的)
回到西安疫情(以及各类天灾人祸),不难看到,祸患未到时,岁月静好,平安无事;灾难一旦降临,系统就运转失灵,显露千疮百孔。这恐怕不仅是“系统性溃败”,而是系统性质的原因。长久以来,人类一直面临着一个最古老的政治哲学困境:如何能够有一个统治权力同时又保持它的驯服状态?如何能够限制其强制力的滥用而同时又不削弱其实现必要功能的能力?如何使权力的边界有所限制而又使之不得放弃责任?
迫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现实世界岂止是西安?又岂止是新冠?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赞(15)
|